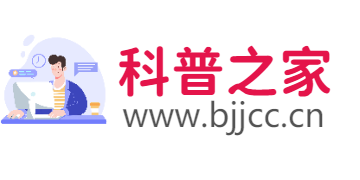《舱外》期刊第三期 如流星般
时间:2023-06-16 01:45:03 来源:科普之家 作者:高校科幻 栏目:科幻 阅读:93
“妈妈说,她不要我。我该怎么办?”
邓秋打字的手停了下来,头从屏幕后面探出去,看前方那个穿蓝色背心的小女孩。
屏幕中的表格已经写好女孩的信息,现在只需填写她的“目标母亲”,她就能从转生局大厅右侧方的门出去,获得自由。然而女孩把头偏向一边,不愿意和她对视。
“她说了什么?”邓秋问。
女孩低下头,玩衣服的一角,那里已经被她捏出几道皱巴巴的折痕:“妈妈说,她希望我是个健康的男孩。男孩可以不用受很多伤害,”
“秋,外面很多伤害吗?”
邓秋不知该如何回答女孩。但是没有目标母亲的话,意味着女孩不能离开这里,暂时没有自由。邓秋将手头的工作停下。
屏幕调至休眠状态,邓秋想了想,拿起桌上的巧克力递给女孩:“或许你需要重新选一个正在备孕的母亲,走吧,我们一起去。”
女孩接过巧克力,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吃了起来。邓秋在自己的电脑前放了一块标明“暂停服务”的黄色牌子,然后牵起女孩的手,两人走向大厅左侧的走廊。于是邓秋的位置空了下来,原本排在她负责的窗口的孩子,只好另外选择工作人员进行登记。
* * *
她们牵着手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。
尽头有一扇双开的门,门牌写着“阅览室”。邓秋打开其中一扇,女孩先钻了进去。
阅览室仿造地球的样式,书架林立,楼梯呈双螺旋状向上,通过楼梯可以去往其他楼层。此时阅览室内还有其他孩子,大的看起来七八岁,小的也就五岁左右的样子。但邓秋知道,他们每一个都拥有和成年人一样的心智和思维,转生局的孩子们从来都不是孩子。
这些小大人从书架取下一本本砖头一样厚的图书,或站或坐,看得津津有味。邓秋不时能听见有人小声嘀咕“就她了”或是“再看一本吧”。阅览室在不断扩大,书本无论何时都必须保持摆放整齐,每三个小时就有工作人员来整理。这里的每一本书都代表一个即将成为孕妇的母亲,书架将她们以地区、人种、民族归类,而每本图书则记录她们的详细信息。为了呈现给孩子们,在书的第一页会注明母亲们的愿望。选好的孩子会带着书到大厅登记,登记完毕后孩子离开转生局,而书归于原位。登记的时候,有时会遇见一个孩子选一本,有时也会看到几个孩子选同一本。
或许阅览室才是转生局的核心。
蓝色背心的女孩看样子对这里很熟悉。一进门她便松开了与邓秋相握的手,径直走向“亚洲东部”分类的区域。看得出来她精心挑选过,精准地找到书架,踩上凳子,精准地取下那本书。
“这是妈妈。”她给邓秋看。
邓秋扫了一眼封面,看到玉琼这个名字。
女孩为她打开第一页,指着清晰的方块字小声念:“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个健康的男孩。男孩可以不用面对很多伤害,”
“可是我既不是男孩,也不健康。我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”
邓秋蹲下来:“不是的,你很健康。只是那里的维度太低,他们不能了解你。你很厉害的,你可以战胜一切。”
女孩从椅子上爬下来,手里抱着那本书:“我不知道。我希望她至少能听懂我说话。”
“你可以选择她的呀。她不能选择你,但你可以选择她。你去到她身边,把话说给她听,一遍不行就多说几遍,总能听懂的。”邓秋轻声说。
女孩抱着书一动不动:“可是我怕她伤心。”
邓秋转而思索,玉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为什么非要男孩不可呢?如果母亲可以选择孩子,那剩下的孩子们都该怎么办?转生局的容量是有限的。就在她沉浸于思索时,工作人员专门用来联络的手机响了。
宋春问她现在在哪里。
“在阅览室,有个孩子恐怕需要重新选书,我在这里陪她。”
“你在陪她?窗口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来了一大批孩子,我要忙不过来了,”宋春叹一口气,“你快点回去吧。”
邓秋:“我很快就回去,辛苦你们了。”
宋春挂了电话。
事实上,邓秋并没有立刻就走。女孩不愿意更换目标,她也不能强求。但一个孩子一直留在转生局总不是办法,看样子只能让其另选目标,否则就要被退回去了。
她牵起女孩的手,穿过走廊回到大厅。女孩另一只手紧紧抱着那本叫《玉琼》的书。如宋春所言,大厅里多了许多孩子。邓秋小跑回到自己的窗口,将“暂停服务”的牌子撤下,孩子们像鱼一样涌到窗口前。说是窗口,其实更像办理登机牌的服务台,邓秋坐在服务台后操纵电脑,给打印好的许可证盖章。孩子们拿到许可证之后就能去门那边了。邓秋刚撤下提示牌,女孩已坐在她身后的塑料凳上,开始翻阅那本砖头一样的书。
邓秋唤醒电脑屏幕,又想,玉琼是什么样的人呢。
* * *
玉琼姓郝,二十五岁。
和她的大多数同龄女孩一样,读完初中就不再上高中考大学了,要么去技校,要么就去找工作。
玉琼曾有过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,没有编制的那种。在水泥和木板搭起来的房子里,好几个年级的孩子混合在一个班,她教他们语文数学音乐美术,用粉笔在黑板上涂涂写写。
玉琼的好朋友叫家瑛,家瑛在纺织厂工作。她们两个的家在一条街上、相隔不远,因此一起长大,一起上学,后来也常常一起出门上班。前年春天家瑛结了婚,丈夫是相亲来的,玉琼去做了伴娘;秋天的时候玉琼也结了婚,丈夫也是相亲来的,家瑛来做了伴娘。
玉琼的丈夫和她一样年轻,还当兵,要去部队上的。玉琼就跟着丈夫一起去北方,坐很久的车,去有大片大片松林和雪的地方,和家瑛分开了。
玉琼给家瑛写信,家瑛也给玉琼写信,她们不像给父母写信那样报喜不报忧,她们互相诉说苦闷、互相安慰对方。玉琼给家瑛寄北方的特产,家瑛给玉琼寄家乡的辣酱,两个人这样来往一直到夏天——家瑛的孩子出生了。
家瑛的孩子是个女孩儿。
邓秋是知道的。
那个女孩儿曾到她的窗口办过手续,但邓秋不能让她通过。她是个各方面都很正常的孩子,正因如此,邓秋的窗口不能给她通过。
邓秋的窗口上方高高悬挂着一个牌子,“孤独症(自闭症)专用通道”。
转生局只是宇宙彼端中的一个中转站,来自遥远星球的孩子们从这里启程,去往名为“地球”的终点站。人们把从转生局到地球这段高维到低维的旅程叫做“生”,把从地球到转生局,低维到高维的旅程叫做“死”,孩子们就这样在光锥之内航行。
从邓秋这里登记成功的孩子不在少数,他们都从太阳系以外的星系来,来自更高的维度,将时间和语言都用颜色记录,是星体熔炉中幸存的未知行星上的居民,邓秋称他们为“星星的孩子”。
然而他们却孤独。来自宇宙彼端的孩子通常具有特殊的才能,而这种特质在他们由高维转向低维时、往往被压缩成难以理解的形式。最典型的形式是“留声”,他们会像留声机一样,重复听到的某一个词,某一句话。那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超越光速、已在光锥的底端连接,而身体却还留在光锥的顶点。邓秋一时想不到更好的解释,总而言之,就是他们的身体总走在思维的后面,很后面。
那个时候邓秋只好对家瑛的孩子说:“你走错了。”
家瑛的孩子穿了一条黄色的连衣裙,怀里抱着写有“家瑛”的书籍蹦蹦跳跳,最后离开了邓秋的视野。
《家瑛》的第一页也写着:“要一个聪明健康的男孩。”家瑛的愿望后面没有玉琼的那一句后缀。邓秋还想不明白那句后缀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她距离地球实在太遥远了,远到她在转生局已经工作了三十年之久。
人们总把光和时间挂钩,但这里光从高空如流星般划过,时间则如奶和蜜在地上流淌。家瑛的孩子最后还是作为一个女孩去到她的身边。转生局的规矩一向如此,只有孩子选择母亲,母亲不能选择孩子。或许地球上的母亲们应该接受职前培训,她们应当被告知怀孕的种种不适、以及如何接受,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。最重要的是关于怀孕的准备。邓秋见过不少降生之后被抛弃而夭折的孩子,他们太匆忙,总是让人感到无奈、又无能为力——能看到这些,都得益于转生局的星图,“产后追踪”。
负责特殊窗口的邓秋埋头打字。
她刚刚批准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申请。孩子们这时候正排队从转生局的侧门出去。那扇门打开、发出奇异的蓝色光芒,尽头是无法观测的行星景象。
坐在邓秋身后、穿蓝色背心的女孩还在看书。女孩郑重地翻过每一页,确保纸张不会出现折痕。她太喜欢了,喜欢到小心翼翼的程度。
到交接班时间,宋春处理完自己窗口前的申请,走到邓秋这边来。邓秋还在处理手头最后一个孤独症孩子,在电脑上填写表格:多血质。宋春低头看了一眼目标母亲,是个英文名字。她抬头,视线越过邓秋的肩膀,看到穿蓝色背心的女孩,以及《玉琼》。
机器吐出一张许可证,邓秋往上面盖章。
宋春说:“她还是不肯走吗?”
邓秋把许可证递出去:“是啊,你瞧。”
“但是我记得,”宋春皱眉,“郝玉琼已经备孕三周了。没有别的孩子选?”
邓秋:“暂时没有。还没有到强制分配的时候,看她怎么选吧。毕竟她有意愿,不至于落空。”
邓秋没有想过这种问题。最后一个孩子穿过地球之门,在时间加速度的作用下去了宇宙的另一端。大厅陷入短暂的沉默。人生命的形成不在于受精的一刻,而是胚胎生长发育的过程。因此转生局将强制分配定在孕妇怀孕的第八周周末。比如当初穿黄色连衣裙的女孩选择去往家瑛腹中,家瑛那时已怀孕五周。第五周的胎儿只是一堆细胞而已。
眼下,玉琼只是在备孕。
孩子们总是固执,好在还有很多种选择。
时钟指向下午六点,光线正在慢慢变暗。邓秋今日的工作完成,交接的同事已经来了。同事想让看书的女孩尽早离开,伸手去抓她的肩膀。邓秋阻止了,摇头:“让她把这一节看完。”
宋春耸肩:“那就等等吧。”
交接的同事比了个“好”的手势,坐在窗口前开始工作。邓秋总是比其他工作人员更了解这些孤独症孩子,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坐在这个窗口。
女孩认真读完了一小节,抬头飞快的看一眼邓秋,然后将目光挪开。邓秋伸出手。女孩合上书,非常配合的和她的手握在一起。
宋春走在她们旁边:“你们就像母女。你了解她,她需要你。
“尽管你们终将分离。”
* * *
宋春在转生局是个有名的诗人。
据说她来转生局之前,写的诗句附着在轴子上,能够去往宇宙的任何地方。也许兆级、京级甚至垓量级的生物都阅读过她的诗歌,在文字之间倾听她的吟唱。每个音节在宇宙之中回唱,多么浩大的工程。
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转生局的工作。
邓秋有些想不起来自己原来是做什么的,模糊的记忆里,是一大片湿润的土地。她光脚踩在泥土里,任风吹拂,感受大地的呼吸。邓秋对彼端的地球有着美好而舒适的记忆。
蓝色背心的女孩却问:“秋,那里许多伤害吗?”
食堂上方悬浮的小星体保持恒亮,充当白炽灯。盛好的饭菜腾腾冒着热气。女孩吃的是员工餐,邓秋为她多接了一杯果汁饮料。
伤害?
或许女孩想问的是地震,海啸,干旱之类的,可怖的伤害,无能为力的伤害。作为转生局的一员,她不能让孩子对生命感到恐惧。人类虽然渺小,但也能创造许多奇迹不是吗?
宋春放下筷子:“你知道她问的是什么,秋。你知道的。”
邓秋深呼吸。
“春,我有时候真的,”邓秋也放下筷子,“对你的直白感到无奈。不能像你的诗一样委婉?”
她知道她们说的是人祸。
“口头和书面是两种表达方式,你不能指望大家都一样。当然啦,说话也好诗歌也好,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。但我无所谓,我自己喜欢就好了,我才会跑到这儿来工作。你呢,”宋春面向穿蓝色背心的女孩,“你选择自己喜欢的不就好了?”
伤害可漫天都是啊。
女孩盯着书籍眨眨眼。
“她听进去了吗?”宋春问。
“听到了,包括你刚刚说的。”
“你总是比我们更了解他们,”宋春端起餐盘走向回收处,“我真的要怀疑你也是从那里来的。”
邓秋回以微笑。女孩飞快地看了她一眼。
她们离开座位,餐桌上空悬挂的小星体闪烁几下,很快就黯淡下去。
她们走出餐厅。转生局仿造地球采用24小时制,此时天已经将黑了。太空梭在远处的港口着陆,周身闪着几种不同颜色的彩灯,孩子们日夜不停地被送来,在这里中转。不同时制的孩子需要调整时差,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现在正是夏天,晚风柔和而凉爽,邓秋想起《仲夏夜之梦》。
转生局给孩子们安排了四人一间的宿舍。穿蓝色背心的女孩不肯离开,也不肯住在宿舍,邓秋打算明天再去跟管理员说明,今天先将女孩带回自己的房间。宋春的宿舍在另一个区域,于是在楼下与她们分别。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打电话,宋春说。
邓秋的房间布置简单,用于独自生活的一厨一卫,卧室和客厅完全是一体的。她在床的旁边放了一张木桌和一个书柜,上面摆满了纸质书。在数据和实体并存的转生局,纸质书并不难找,难找的是这些具有针对性的专业书籍。关于孤独症、太空、还有星体。在床头柜上还有几张电影CD,封面写着《雨人》,但并没有看到CD机。
女孩拿起CD看了一会儿,放下,翻看随身携带的书本。她看到玉琼的兄弟姐妹那个部分了,似乎不怎么感兴趣,翻得很快。
桌上杯子大小的玻璃生态缸养着两只蓝色球藻,它们贴在一起,偶尔会吐出一颗玫粉色的泡泡。女孩被球藻吸引,放下紧握的书本。她挪动生态缸,球藻又吐出一颗泡泡,飘到水面底下,像两个未成熟的卵泡。然后她把手伸进生态缸里,想戳破那两个泡泡。泡泡却围绕着她的手指,从一端跑到另一端。
她控制不好力度,玻璃杯忽然倾斜、倒下,滚落到地板上,“当”的一声碎成很多片玻璃。两颗球藻安静地从杯子里滚出,落在地上,分散。邓秋听到声音急忙从厨房跑出来,万幸女孩没有受伤,只是玻璃碎了一地。她蹲下去把两颗球藻捡起来,因女孩摊开手,邓秋便把球藻们放在女孩的掌心。柔软的球藻相互依偎,战栗,呼吸,女孩初次体验生命之轻,她无法自控地落下泪来。
邓秋俯身捡拾玻璃碎片,听见女孩的抽泣:
“秋,这是伤害吗?”
* * *
亲爱的玉琼,
你久等了,我现在才来信。
玲儿一直不好,前日才发高烧,现已好转。我趁她睡着,才抽空写信。今天中午去歺厅吃饭,看到你最喜欢的鸽子汤,想起我们小时候一起去捉鸽子,摘菠菜,才觉那时轻松自在。
前几日取到给玲儿拍的相片,眼睛鼻子都像我,因此寄给你也看看。我给玲儿看你的相片,说你是她的干妈,玲儿高兴得直笑,想必她也喜欢你的!
你在部队过得好吗?不要劳累,我做了些豆瓣酱给你。
期盼你的来信!
想你的家瑛
信封里装着一张相片,孩子的头发很短,毛茸茸的一片贴在头皮上,穿一身浅色的连衣裙,坐在地上玩玩具。大概有人逗她,她水润的大眼睛盯着镜头,就像隔着遥远的时空在和自己对视。眼睛和鼻子真像啊,还有这张小嘴巴,要是眉毛长出来细细窄窄的,那简直就是家瑛的翻版了。玉琼看着照片露出笑容。
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家瑛的女儿都满月了,夏天已经过半,再一转眼就要秋收。秋收之后就是冬天,北方总是很冷,到处都是冰雪。听猎户说林场那边有野兽,尤其是蛇,玉琼从来不敢一个人去。
浆洗衣服的时候她想,要是自己是个男孩儿呢。
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,她书没念完就出来工作,工作不久就结婚走了。没办法,丈夫要当兵的嘛。大一点的弟弟去省外念书,小一点的还在上小学,最小的妹妹寄到乡下去养了——爸妈死得早,玉琼没有办法。
好不容易在部队稳定下来教教识字什么的,婆家那边催着要孩子。大的都养不活,还忙着要小的,玉琼跟丈夫说。好在丈夫知道体贴她,跟她说咱不着急。
玉琼想,要是自己是个男孩儿,说不定可以继续读书,可以继续教书,不用来冰天雪地的东三省呢?
但这样的话就不能和家瑛亲密无间,不能做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了。不能一起捉鸽子,去别人菜地里摸花生,不能卷一张被子躺一张床一起睡觉了。这对玉琼来说似乎更加难以接受。
那要是娶家瑛呢?
她被自己的想法逗笑。要是她娶家瑛,肯定会对家瑛好的。
晾好衣服她回到屋子里,打开豆瓣酱的罐子闻了闻,又满意地封好放在床底下。玉琼拿出丈夫的钢笔,墨水和信纸,看着窗外的床单被罩给家瑛回信。鸽子从打靶场上面飞过,孩子们正在太阳底下滚铁环。
亲爱的玉琼,
思念你。
听你说除教写字认字之外还要洗衣做饭缝缝补补,总怕你冻伤。你之前就爱生冻疮,记得擦药,不要怕麻烦。
玲儿又发高烧,好险才降下来,我急着含着眼泪盼她健康。给你写信已是深夜,我实在害怕,难以入睡。
你一定保重身体,千万不要勉强,孩子也不用急着要。近来家里实在太忙,没能做些东西,希望你不要生气。
思念你,等候你的来信!
想你的家瑛
都忙成那样,还要让自己不要因为没有礼物而生气,玉琼悄悄在心里骂了家瑛两句。又不是为了礼物才写信!其实在部队比在家里要稍微轻松一些,没有那么多人要养。玉琼摸信封里面,没有摸到其他东西。
信里没有捎上好友的近照,连玲儿的也没有,玉琼看着面前漂亮细瘦的方块字发呆,也不知道她们过得怎么样。玲儿身体不大好,老是感冒发烧,也不知道带没带去诊所医院看看。都这样事了,光吃感冒药怎么行?
玉琼真想一个长途电话打去。
可今天她要去帮忙做饭。部队这几十几百号人都在食堂吃大锅饭,她们得去搭把手。这样一来还有打电话的时间吗?玉琼边系围裙边计算着:打长途电话得排队,吃完饭要洗碗,那时肯定来不及;不吃饭直接去,打完回来饭估计也没了——天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胃;那就打好饭,捡点菜搁碗里,端着去排队就是了,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就这么办吧。玉琼去洗菜择菜,把刮刀洗干净好削山药皮。
无论红案白案,厨房里一切操刀的都是力气活。剁肉、削皮、切块,只要是这个厨房里的女人,你给她一把刀,她就能杀出满汉全席来。她们总有魔法,把最普通的食材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端上饭桌,变成世界上最难以抵挡的味道。这些菜各式名字,种类繁多,而归根结底笼罩其之上的,就是女人们的“家常”。
玉琼没有分家瑛做的豆瓣酱。炒菜的时候她分神去想先藏在床底下后又挪到家中小厨房的小罐子,想那里面香得发闷的豆瓣酱,手被溅出来的油烫了一下,她手一抖,然后轻声的笑。别人问她乐什么呢,她说没什么,开心呢。她那时候二十四岁,还能自由自在地开心着。
最后她如愿端着饭盒排到长途电话的队伍,拨下家瑛的电话号码。她记得她的家里有台座机,虽然有点旧了,但一直都可以用。
电话通了,玉琼斟酌如何开口。好友已经是妈妈了,那她是否要用干妈的身份关心点什么呢?先喊瑛子,问她近日怎么样,然后问玲儿怎么样,问家里养的猪长得好不好,地里的菜……有点不知道从何说起,先就这样问吧。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忙音。估计在忙着给玲儿喂奶喝药什么的,玉琼一只手端着饭盒,另一只手拿着听筒。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还是忙音。
可能在睡午觉,没有听见。没事,再响两声就听见了。玉琼拿饭盒这只手有点酸,但她不敢换手,她生怕换手的一瞬间电话接通,家瑛听不见声,给她挂了。玉琼就这样保持单手端饭盒单手拿听筒的姿势,像一尊雕塑。
嘟——
嘟——
嘟————
无人接听。
直到最后还是无人接听。没人收取她打长途电话的费用,可玉琼看起来就像付了十倍的价格。家瑛怎么会不接电话呢?她想不明白。
* * *
女孩不能留在这里太久。
邓秋被这样告知。
转生局的容量有限,确实不应该收留孩子住在这里。要是想长期待在转生局,只有成为这儿的员工。
可女孩太年幼了。从她踏进转生局的那一刻起,八周的倒计时便开始,时间一到,她只会被强制送走。与其被随机安排,不如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个好妈妈。
邓秋在闲暇之余去阅览室检索关键词,输入“男孩”“不受伤害”,弹出的结果数不胜数,她换了关键字,输入“女孩”“伤害”,检索结果是刚刚的十倍之多——不包括意外伤害。
阅览室的书籍全都是女性,身为女性光是生产的痛苦就超越了大多数事件,而这些事件都被记录在册,装订成书。
那么玉琼是为了这样的事才想要一个男孩吗?除非她的愿望改变,或者转生局真正理解她的想法,那个穿蓝色背心的孤独症女孩才能够去往她的身边。阅览室的书籍太多了,不可能每一个都像这样挨个去了解,那以后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?邓秋撕下便签纸放进口袋。催促孩子们在并不懂宇宙彼端的情况下做出选择,是否也算是残忍?
太空梭船舷之外四十八万公里的地方,一颗垂死的恒星正在闪烁,其闪烁的频率宛如发送视觉信号。信息以光速发送到转生局,而时间却被延长,使得转生局能在第一时间获取来自宇宙的信息,并且有成倍的时间来进行分类处理。这很奇妙,邓秋想,或许这就是预言。
显然外星来的女孩比邓秋更懂这个道理。在她眼里,母亲的愿望就像宇宙,而宇宙是一个盛满水的水杯,他们所在的位置只是一个气泡。光径直穿过水体和气泡,而时间则以冲剂粉末的形式缓慢融化并作用于整个宇宙——这也是为什么她的思维总走在前方——她的目的地地球,只是水杯中的一颗蓝色球藻。
不了解妈妈、毁坏妈妈的愿望是一种伤害。
毁坏之后任其痛苦不管不顾也是一种伤害。
对妈妈的伤害。
邓秋收回目光。
垂死的恒星由内而外爆炸,生成一朵蓝紫色相间的星云,一道光圈在毫秒内向外蔓延出数千公里,或许彼端的地球能够观测这颗恒星最后的信息:你好吗,宇宙那端。
有一阵清凉又爽快的风,从舷窗的缝隙吹进来,把女孩额前的碎发吹动,把她摊开的书页吹动。《玉琼》摊开放在邓秋的床上,风把它吹到“玉琼与家瑛”的章节,两个好朋友如星星般,在恒星之风中翩翩起舞。
女孩垂下视线,她已经画了好几幅完成度很高的画,内容以圆圈和曲线为主,是气泡、星球、时间粉末、球藻、装豆瓣酱的罐子、横跨纸张的电话线。孤独症女孩的语言很少,每当她把画给邓秋看,邓秋便觉得她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对能够轻易读懂画的邓秋来说,这个故事并不温馨。
就算是邓秋也忍不住开口问,那种选择玉琼的信念从何而来?
女孩翻动书页,指着玉琼幼时穿蓝色毛线衣的照片。
邓秋问还有其他原因吗,就因为这张照片你能为她放弃一切?
女孩回忆起初次进入阅览室的经历,身体本能地向温暖的地方走去。她穿过林立的书柜、走上双螺旋的扶梯,甚至爬上椅子,手就这样触碰到了玉琼。翻阅书籍的某一刻她听到女人抬头仰望天空说:如果我的孩子来自星星,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爱她。一瞬间她的脑海里像有什么东西归位。
她说:“为了不伤害妈妈,我只是在等待。”
邓秋把手伸进口袋,去捏那张便签。上面写着宋春说过的词:母女。
* * *
家瑛怀孕之前做了个梦。
在梦里家瑛的身体如羽毛一样轻柔,轻轻点地就能飞上高空。
于是她享受着不受束缚的自由,欢快地往上飞行,愈来愈上,能够俯瞰乡村、城镇、国家、地球。
家瑛一点也不害怕,她在空中挥动双臂,舒展着自己的身体。她在梦中忽然有了一个概念:宇宙、太空。
她想:宇宙是什么?太空是什么?
接着家瑛去探索宇宙,她路过土星的星系带,路过仙女星云的大星云,在她返程路过月球的时候,忽然看到一束光从遥远的地方向地球而去。
那是什么?
来自宇宙的光有些刺眼,家瑛眯着眼睛追寻光的来处,有一束漂亮又独特的光冲进她的视野。那道光的顶端是蓝色,拖尾却是好看的明黄,像穿着一条黄色连衣裙。光从她的耳边划过,她听到叮叮咚咚的声音,像小时候用贝壳和碎玻璃做的挂在屋檐下的风铃。
光从耳畔消失后,家瑛的视野慢慢变暗,她渐渐醒来。醒来后她对自己的丈夫说:做了一个怪异的梦。
什么样的梦?丈夫问。
记不起来了,好像是太空。
太空?丈夫想了想,说好像梦到太空容易生男孩。
* * *
亲爱的玉琼,
又是一个明媚的春天了。
之前你给我打的电话我没有接到,那天正好去拿药,家里没有人。我给你打过去,电话一直占线,不知道是不是座机出问题。
玲儿不见好,乡里的大夫没有办法,让我们去县里。这是我在县里的招待所写的,希望明天一切顺利。
回信地址还是用家里那个,期盼你的回信!
想你的家瑛
信是拿日历写的。旧日历的纸很硬,正面是女郎画片,背面却会掉白色的粉。家瑛用圆珠笔写字不如用钢笔写字好看,那圆珠笔还漏墨水,一块儿深一块儿浅的。
玉琼把信拿给丈夫看,想汇款过去,替家瑛分担一些,丈夫同意了。可等她电话打给招待所,对面的人说家瑛她们带着孩子已经走了。
已经走了啊。玉琼洗衣服的时候一直想着,忘记清了几次水,只是按照肌肉记忆将丈夫的外套拧干。北方春天化雪,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。她手上的冻疮隐隐有些发痒,低头一看、已肿了一大圈了,十根手指,五根肿得像小萝卜。
家瑛怎么样了呢?玲儿怎么样了呢?
玉琼想着、想着,直到睡觉之前都还在一直想着。
后来隔了很久家瑛也没有信来。
玉琼等不了了,托人去找,又托人带了钱。
辗转两月,终于有了家瑛的消息,说是人已经整个都憔悴下去了。
不可能,你找错了吧?玉琼不相信。她在部队看过家瑛寄的照片,虽然生了孩子,精神气都还在的。家瑛身体虽比不上她,但肯定是很好的。她坚信那人找错了。
带话的人直摇头,把照片递给她。玉琼几乎抢过照片迫不及待地看:细细窄窄的眉,杏眼,有一点外突的嘴……不同往日那张圆润的脸,家瑛竟然干瘪下去了。玉琼眼里蓄满泪,问带话的人:她怎么了?
太劳累了?病了?玉琼不敢想更坏的事情。
“她女儿高烧,烧糊涂了。”
玉琼一愣:“什么叫烧糊涂了?”
“就是没救了,成傻子了!”
玉琼急了:“你说仔细些,怎么就、怎么就没救了!你说呀!”
“家里人带到县医院去看,县医院治不了,要转省里。说是没钱了,拉回家里吃土方子,等退烧了,娃也傻了。”
玉琼怔怔。
怔怔。
半分钟过后,她回过神,几乎扑到电话前去拨家瑛的号码,一次,两次……最后电话终于接起来。
她在电话里大骂:“李家瑛!她是你的女儿啊!”
骂完她开始哭,哭得眼泪把衣服都打湿了。家瑛也一直哭,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家瑛手里攥着玉琼托的人带来的钱。可是已经没有用处了,她手里紧紧攥着,好像握着女儿的命,稍微一松手女儿就要像那道黄色拖尾的流星般消失。
玲儿在睡觉。玲儿睡着时看不出来有其他任何问题。家瑛压着声音哭,抽泣。她说:“玉琼,我想去省里的。”
“婆婆说为一个女孩治病浪费钱。我又哭又闹,他们硬把我拖了回来。”
“他们说女孩吃点苦头就吃吧,”
“可这是为什么呀?”
家瑛又断断续续地哭起来:“玉琼,玉琼,你的孩子千万不要像我们一样。”
玉琼在电话的另一边呜咽。
长途电话的时间到了,通话于是切断。
玉琼终于忍不住,将听筒抱在胸前,放声大哭起来。
* * *
邓秋无意中发现《玉琼》的第一页有涂改的痕迹。
任何人无法对阅览室的书籍进行修改,无法毁坏、涂抹,除非是郝玉琼本人。
那么原本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呢?
她从女孩那里要来书籍,翻过第一页来对着窗外照进的太阳。“男孩”两个字底下有涂改液的痕迹,那是玉琼的意识。涂改液和纸张几乎融为一体,透过光,可以辨认出左右颠倒的字迹:“女孩”。不止这一处,就连后面的那句后缀,原本写的是“像我和家瑛一样”。
邓秋的心狠狠地堕了一下。她并不知道在三十年之外的宇宙那端发生过什么事,产后追踪只能看到家瑛的孩子还活着,并不知道活得好不好。
邓秋站在写有“观星室”门牌的房间里。
墙壁上挂着一幅星图,众多星星之中虽有空位,但它们基本上都保持常亮。一颗星星熄灭,意味着一个孩子夭折。转生局用来保管信息、观测结果的设施布置得很好,唯独那扇门,那扇象征生命和自由的太空之门,就那样随便放在大厅一侧。几十年来,大家看着无数孩子从那里飞出去,去宇宙那端,光和时间重合,时间不再以曲速前行,重合的一刹那孩子们的生命真正开始流动。
邓秋在斟酌。直接告诉女孩的话,她会欢欣雀跃而立刻投入妈妈的怀抱吗,那郝玉琼呢?其中的缘由邓秋还需要再了解吗?
愿望在转生局代表本能和意识,存在于基因的本能,由大脑控制的意识,几乎不会被修改。一定发生过什么。邓秋决定暂时不告诉女孩。
宋春带来转生局内部的消息,女孩必须回到孩子们专用的宿舍,邓秋不能和女孩住在一起。
女孩正午睡,邓秋端来一杯果汁,顺手去给球藻换水:“是吗……”
“你怎么打算呢?还有三周,三周之后她就到期了,要么强制分配,要么就退回到原本的星球上去。她肯定一个都不选。”
邓秋笑了一下:“连你都清楚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宋春余光看到床上的两个枕头,桌上的两个杯子,地上的两双拖鞋。她忽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:“呃,秋,你最好不要想。”
邓秋的动作停了下来,透过生态缸的水体看缸中的球藻。两颗蓝色的球藻在水底紧紧地贴在一起。邓秋有一双棕黑色的眼睛,像是秋天的栗子和核桃的颜色,被这样的眼睛凝视,更多的时候会感到亲切和安心。
“我在想,如果她选我呢?”
邓秋继续说,“工作守则上没有说不可以在这里领养孩子。”
宋春表情平静:“这是领养吗?”
“我会争取。”
“你只不过是想把她留在这里。”
“有什么不好呢?既然她只是在等,不如就让她留在这里,等玉琼在到期之前想通了或者等她找到新的、爱她的,不就好了?”
“那到底是谁在等?”
宋春站起来,扭头看着在一旁午睡的女孩。女孩呼吸均匀,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毛绒玩具,《玉琼》放在枕边。
“我很庆幸我们还是朋友,而你提前告诉我这件事。没有人比你更懂这些孩子了,等也好怎么样也好,你必须听从她的意愿。只有她才能选择谁做自己的母亲,”宋春仰头把果汁喝完,微微抬起杯子向邓秋示意,“果汁很好喝。”
宋春离开了。她就像春天那样,来无影去无踪,就连爱也难以表达。
宋春离开后,邓秋坐下来。她坐在自己并不算柔软的床上,女孩睡在靠墙那一侧。书的封面是皮革,光滑,富有弹性,来自亚洲东部的标签静静贴在书脊底端,封面写着方块字,没有姓氏,只有名字:玉琼。
睡着的女孩与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。柔弱,脆弱,稚嫩,如天底下所有的孩子一样,她有着一张漂亮而独特的脸。
邓秋翻开这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书,这本记载了玉琼在成为一个母亲前的所有生活。每个孩子都不曾了解也无法想象的,妈妈还不是妈妈的时候的生活。她的幼年、青春、喜恶;朋友、家人、心结;不舍、后悔、勇敢;牵挂、思念、初恋。方块字写下十二划,写成“妈妈”这个词。在三十年短暂又漫长的孤独里,邓秋第一次坐下来了解宇宙彼端的某个母亲。
然后邓秋质问自己,是否有勇气成为一个母亲。
要如何教导一个孩子呢?
又如何教导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呢?
从呱呱坠地,到牙牙学语,理解她的世界,学习她的语言,直到她长大成人,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剖开邓秋的世界、然后离自己而去。宋春说过她们就像母女,邓秋了解她,她则需要邓秋为她解答世界的答案。可要是一直待在转生局这方天地,总有一天她会向往宇宙彼端。她会走的。
伤害漫天都是。
邓秋的眼泪忽然落下来。
* * *
玉琼做了一个梦。
她梦见一条碧绿如玉的小蛇,从林场爬到她的房间门口。
丈夫不在身边,玉琼说不上是害怕还是担心。她透过窗户看那条小蛇,小蛇只是静静地等在外面。
她梦见外面开始下雨,像眼泪掉下来一样的下雨。小蛇没有地方躲雨,只好跑到屋檐下。屋檐下有一只贝壳和碎玻璃做的风铃,伴随雨声发出好听的叮叮咚咚。
玉琼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,把门打开,让小蛇进来避雨。
小蛇有一双蓝色的眼睛,只是和她遥遥相望。她们一直相望着、相望着,雨声嘀嗒,风铃清脆,
小蛇喊:妈妈。
它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小女孩,让玉琼忽然想起自己幼时。不用辍学,不用养家糊口,不用被迫奔波。玉琼指自己:在叫我吗?
小蛇又说:我好想你。
玉琼忽然发现自己的孩子竟跟自己全然不同,那样漂亮的小蛇,为什么一定要认自己做妈妈呢?他跟丈夫只是恰巧有些积蓄,婆婆又催着要一个孩子而已。
我和别人不一样,妈妈你会不会难过?小蛇问。
怎么会难过呢,玉琼心想,她高兴还来不及。自她决心成为母亲之后,这句话在她心里已说过无数次:
无论是说话还是示范,我会为你千千万万遍。
话还没说出口,雨渐渐大起来,声音盖过一切,视野变得朦胧又黑暗。
玉琼醒来。
她去摸枕头底下放着的家瑛的来信,她们很快就会从大山之中的盆地到东三省来了。
* * *
“妈妈说,她不要我。我该怎么办?”
邓秋回想起第一次和女孩见面的时候她说的话。
郝玉琼原本的愿望不是这样。邓秋知道,她的愿望曾经是: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个健康的女孩,像我和家瑛一样。
女孩仍然日复一日地观察球藻,日复一日地读书。邓秋知道,她很爱玉琼,她在等待。
太空梭又一次降落在转生局前边的港口,又有几个孤独症孩子来了。这是那个女孩留在转生局的最后一周了。
邓秋挑了轮休的这一天将所有事情告诉女孩。包括玉琼原本的愿望,第八周的期限,以及可以选择做她的孩子。做邓秋的孩子,不用等待。
听完后女孩问了最初的那个问题:
“秋,外面很多伤害吗?”
邓秋蹲下来,女孩仍然没有与她对视,只是盯着邓秋领口上的纽扣。她有义务让孩子明白宇宙彼端会发生的任何事情。
“是的。除了天灾,还有许多人祸。”
“人祸是什么样的?”
“你可能会因为不被理解而被嫌弃、被抛弃、被背叛,会面临不公,会有难以逾越的难关,会仿徨挣扎却得不到答案。”
你的特质,会让你遭受更多的考验。
“那时我怎么办?”
邓秋笑起来:“一个人硬撑是走不下去的。求助爱你的人,爱你的人一直在等待你的求助。”
“妈妈会爱我吗?”
“她会给你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爱。她的爱源源不断,永不枯竭。她的爱存在于你身体的每一处。”
“哪怕我来自别的星球?”
“你是她的孩子。”
女孩在邓秋的窗口前递上书。
“秋,我能回应你的问题吗?”
“是哪一个?”
“所有的。
“我也爱你,秋。”
回应并非终点,而是如转生局一样,只是转折。她在这里得到的春秋之爱,宇宙之爱,足以推动一颗星星前行,也推动邓秋继续前行。
此后千千万万个孩子经过此路,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,邓秋也能从容应对,指引孩子去下一处生活。
此时《玉琼》的第一页,愿望已变为最初的愿望,只是不是“像我和家瑛一样”,而是“能成为她想成为的人”。玉琼正在丰饶的秋天,等待。鸿雁飞过,小麦成熟,她正等待。家瑛在土地的另一边已经收拾好行李,要带着玲儿去找玉琼。她们用长长的电话线和一封封信件将命运的土壤连起来,好让将至的孩子安稳降落。玉琼正等待朋友和孩子的到来。
“妈妈需要我。”她说。
“是的,她需要你。来吧,”邓秋让电脑吐出许可证,然后盖章,指引她去大厅右侧那扇绚丽奇妙的门,“出发吧。”
宋春在门旁边等。门就像一个漩涡。宇宙此端前往彼端的漩涡,通过此门,高维压缩成低维,记忆被拆散,意识回到最初,生命彻底融入光锥,不可逆转。
她站在太空之门前,最后回头看邓秋:“再见,秋。代我向妈妈问好。”
然后纵身一跃。
她就这样如流星般,从宇宙此端降落到妈妈身边。
本文链接:https://www.bjjcc.cn/kepu/82208.html,文章来源:科普之家,作者:高校科幻,版权归作者所有,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!
上一篇:第3期舱外本期执行主编的话